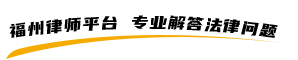探望權糾紛中,我們最常見到的是直接撫養子女的一方要求另一方減少探望、不予配合,甚至請求中止對方探望。這類情形下,法院可根據具體情況依法采取強制措施。
然而,還存在一種相對少見的情形,即非直接撫養方怠于行使探望權,而直接撫養方為了孩子的身心成長,希望對方履行探望義務,卻遭到消極對待。此時,能否通過法院強制執行對方來看孩子?
在現階段,法院對探望權案件的執行持審慎態度。因探望行為的人身屬性及執行難度,我們在檢索時也少有發現支持直接強制執行的案例。多數法院認為,探望權的行使與否原則上由權利人自主決定,通常不會強制要求權利人履行探望義務,建議多通過法制宣傳教育、思想說服教育等方式促進自動履行。
如(2019)蘇1202執719號裁定書中指出:“是否行使探視權是申請執行人的自主行為,只有在另一方當事人阻止或不配合探視,也就是存在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情形,才能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可見,法院的強制執行措施針對的是“阻礙探望”的行為,而非“不探望”的行為。
對于這個問題,蔡律師傾向意見是,從法律理想狀態而言,探望權實際應具備可執行性。從子女本位出發,若在未成年子女成長有需要的情況下,不直接撫養方不積極履行探望義務,將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離婚后,不直接撫養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應當依照協議、人民法院判決或者調解確定的時間和方式,在不影響未成年人學習、生活的情況下探望未成年子女,直接撫養的一方應當配合,但被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權的除外。”條文連續使用兩個“應當”,體現出立法者對探望行為不僅視為一項權利,也強調其帶有義務屬性。探望既是父母與子女保持情感紐帶的重要方式,也關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與人格健全。
如果確有強烈需求,一種可行路徑是以未成年子女的名義提起訴訟,請求法院通過裁判明確探望的時間、頻次與具體方式,將被動等待變為主動確權。
在(2022)豫0702民初1894號判決書中,法院采納了類案觀點,認為“本院通過類案檢索,發現在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山東省威海市環翠區人民法院等法院關于類案的處理中認定,‘探望權是不直接撫養方基于父母子女身份關系而派生的一種法定權利。對于不直接撫養方而言,既是一種權利,也應是一種義務,當其不履行探望義務時,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探望子女不僅僅是父母與子女的見面和團聚,更是父母及時了解子女生活和學習情況的過程,是父母與子女溝通交流和精神撫慰的過程,也是子女感受父母關愛促進自身健康成長的過程,因此,父母對子女進行探望,不僅是父母的權利,也是履行對子女進行撫養、教育的法定義務。’本院對上述裁判思路也予以認同。具體到本案,原告尚未成年,希望得到父親的關愛和教誨,實屬法理情理之中。被告通過探望,可更好地了解原告的成長、學習、生活情況,有利于彌合因父母的錯誤行為帶給孩子的感情傷害,故對于原告要求被告探望的訴請,本院予以支持。”
但此類訴訟的難點在于,即使得到法院判決支持,在實際履行中仍可能面臨執行難的問題。法院一般僅能對拒不配合的一方采取罰款、拘留等間接強制措施,而不能直接強制對方履行探望行為。
蔡律師認為,在離婚協議、裁判文書已經明確探望時間、地點、方式的情形下,權利義務實質已明確,應當具備可執行性。若因不直接撫養方不積極履行探望義務,就要求直接撫養方或子女通過另行訴訟解決,無疑增加當事人訟累,也有損子女最大利益原則。
福州律師蔡思斌
2025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