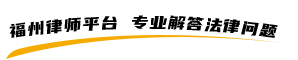企業(yè)經(jīng)營中,常有“公款轉(zhuǎn)入私人賬戶”行為,該操作看似滿足客戶需求的靈活操作,實則暗藏致命的刑事風險。某省公安廳督辦的一起案件便是深刻教訓:一家票據(jù)中介公司應客戶要求,將扣除貼現(xiàn)利息后的票款(屬公款性質(zhì))轉(zhuǎn)入指定私人賬戶,最終因涉案金額超1000億被控非法經(jīng)營罪。公安機關(guān)對這家家族企業(yè)全員采取強制措施,實際控制人及其父兄嫂均被羈押,僅妻子因參與度較低未被刑拘。雖然案件過程驚心動魄,但經(jīng)律師辯護取得了較好效果,審判階段檢察院撤回了起訴,最終對當事人一家做出了不起訴決定。
法院階段達成的關(guān)鍵共識在于兩點核心辯護意見:
一是票據(jù)買賣本身不宜入罪。辯護人援引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買賣銀行承兌匯票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意見》(高檢函字〔2013〕58號)。該批復明確指出:“根據(jù)票據(jù)行為的無因性以及票據(jù)法關(guān)于匯票可背書轉(zhuǎn)讓的規(guī)定,匯票買賣行為不同于支付結(jié)算行為,將二者等同可能會造成司法實踐的混亂…對于單純買賣銀行承兌匯票的行為不宜以非法經(jīng)營罪追究刑事責任。”法院采納了這一觀點,認為本案的核心業(yè)務模式是買賣票據(jù),其本身不宜被認定為非法經(jīng)營罪。
二是票據(jù)買賣行為本質(zhì)雖涉套現(xiàn),但未獲利。辯護人承認,中介應客戶要求將資金打入其指定私人賬戶的行為,本質(zhì)上幫助持票人實現(xiàn)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辦理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jié)算業(yè)務、非法買賣外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一條第二項明確規(guī)定的“單位銀行結(jié)算賬戶套現(xiàn)”及“單位銀行結(jié)算賬戶轉(zhuǎn)個人賬戶服務”情形。然而,重點在于,中介在此特定環(huán)節(jié)并未因此“套現(xiàn)服務”向客戶額外收取費用或獲利。辯護觀點認為,非法經(jīng)營罪的構(gòu)成不僅要求行為違反國家規(guī)定,通常還需具備經(jīng)營性和營利性。在此案中,中介提供“轉(zhuǎn)私戶”服務只是為了滿足客戶要求、避免客戶流失,屬于其整體票據(jù)買賣業(yè)務的附帶行為,本身并未單獨牟利,因此不應單獨構(gòu)成非法經(jīng)營罪。
盡管最終結(jié)果是相對理想的“不起訴”,但企業(yè)業(yè)務因此停擺兩年,家庭瀕臨破碎——這一切的導火索,正是批量“公款轉(zhuǎn)私戶”的操作,觸碰了《解釋》中“單位賬戶向私人賬戶違規(guī)套現(xiàn)”的法律紅線,并引發(fā)了漫長的刑事追訴程序。這警示我們:即使核心業(yè)務模式可能獲得司法上的非罪評價,一旦涉及“公款轉(zhuǎn)私戶”操作,就極可能引爆刑事調(diào)查程序,帶來難以承受的代價。
公款轉(zhuǎn)入私人賬戶的操作,是票據(jù)中介業(yè)務中最危險的環(huán)節(jié),極易引爆多種刑事風險。首先是非法經(jīng)營罪(核心風險):長期、大量將本應在對公賬戶流轉(zhuǎn)的公款,通過私人賬戶轉(zhuǎn)移,特別是中介在此環(huán)節(jié)收取額外費用獲利,極易被認定為《解釋》第一條所界定的“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jié)算業(yè)務”。根據(jù)《解釋》第三條規(guī)定,非法經(jīng)營額達500萬或違法所得超10萬即構(gòu)成“情節(jié)嚴重”,應追究刑事責任。
陳立志案[(2019)豫0928刑初775號]就是典型印證:中介通過空殼公司偽造貿(mào)易背景向銀行申請貼現(xiàn),將本應進入對公賬戶的貼現(xiàn)款(公款性質(zhì))205億元,通過其控制的公司賬戶周轉(zhuǎn)(本質(zhì)仍是公款私戶化操作),被認定為“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jié)算”,最終被判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罰金8000萬元,追繳違法所得7400萬,成為“九民紀要后民間貼現(xiàn)入刑第一案”。
其次是洗錢罪:若明知轉(zhuǎn)入私人賬戶的公款來源于賭博、詐騙、走私、貪污賄賂等違法犯罪活動,仍協(xié)助轉(zhuǎn)移、掩飾,則可能構(gòu)成洗錢罪,最高可判處10年有期徒刑。根據(jù)《解釋》第五條,若同時構(gòu)成非法經(jīng)營罪與洗錢罪,需依照處罰較重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
深圳某票據(jù)中介協(xié)助北京某青城公司案(2024)中,該票據(jù)中介被認定的“公轉(zhuǎn)私”金額,均為某青城公司要求轉(zhuǎn)賬的“職務侵占”違法犯罪款,法院判決凸顯了此類犯罪“為他人違法犯罪資金提供結(jié)算服務”的實質(zhì)[北京東城區(qū)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24)京0101刑初40號;(2023)京0101刑初648號]。
此外,逃稅罪也不容忽視,公款通過私戶流轉(zhuǎn),容易導致收入隱匿、貼現(xiàn)利息支出無法取得合規(guī)發(fā)票進行稅務處理,一旦被稅務機關(guān)稽查認定偷稅,且偷稅比例超過10%,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同時,還可能涉及其他關(guān)聯(lián)犯罪,如職務侵占罪(若挪用客戶票款)、詐騙罪(若參與偽造材料)、共犯風險(若明知資金性質(zhì)仍協(xié)助轉(zhuǎn)移)等。
針對公款轉(zhuǎn)入私人賬戶的風險,避險的核心在于切斷“公款私轉(zhuǎn)”的鏈條。資金流要嚴格隔離,堅決拒絕經(jīng)手私人賬戶!要求付款方,無論是銀行還是下家,必須將扣除利息后的凈額(即公款)直接轉(zhuǎn)入持票人(即票據(jù)權(quán)利人)指定的對公賬戶,并且完整留存清晰、可追溯的資金流水憑證。
同時,要嚴守“三不”原則:
一是不偽造,絕不參與偽造貿(mào)易合同、增值稅發(fā)票等材料申請貼現(xiàn),以避免卷入詐騙、逃稅共犯;
二是不代持,不代替客戶持有票據(jù)或控制其資金賬戶,以防范侵占、挪用指控;
三是不經(jīng)手利差,中介的合理服務費應與票款本金嚴格分離計算和收取。絕對避免在“公款轉(zhuǎn)私戶”環(huán)節(jié)收取任何形式的額外費用或利差,這是證明其未達到《解釋》第三條規(guī)定的“違法所得超10萬”入罪標準的關(guān)鍵。
另外,要強化合規(guī)審計,定期進行專項審計,重點核查票據(jù)來源合法性,排除盜搶、詐騙等非法所得票據(jù);資金流向合規(guī)性,確保票款流轉(zhuǎn)全鏈條均為“公對公”記錄,無任何私人賬戶介入;稅務申報一致性,服務費收入必須與完稅憑證嚴格匹配,杜絕隱匿收入。
開篇所述千億票據(jù)案最終不起訴的關(guān)鍵在于“未獲利”(即未達到《解釋》中違法所得標準)和“票據(jù)買賣本身非罪”的辯護成功,但這絕不意味著“公款私轉(zhuǎn)”行為本身無風險或可僥幸嘗試。它恰恰是引爆刑事調(diào)查程序的導火索,其帶來的強制措施、財產(chǎn)凍結(jié)、業(yè)務停滯、聲譽損毀等過程代價,對任何企業(yè)和家庭都是毀滅性的。
陳立志案的天價罰沒和深圳中介案的共犯認定,更是清晰展現(xiàn)了觸碰紅線的慘重后果。對票據(jù)中介而言,“公款絕不入私戶”必須成為不可撼動的鐵律底線。一次看似簡單的違規(guī)操作,就可能成為引爆企業(yè)和家庭的“定時炸彈”。在金融合規(guī)日益嚴格的背景下,唯有堅守這條鐵律,才能在復雜環(huán)境中規(guī)避最致命的刑事風險,求得生存與發(fā)展。畢竟,貼現(xiàn)的利差可以計算,而牢獄之災和天價罰金的代價,永遠無法估量。
福州律師蔡思斌
2025年8月1日